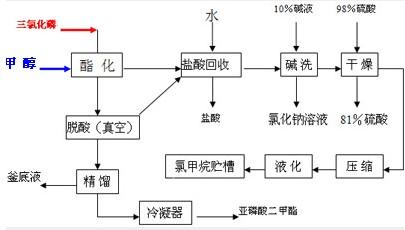在我们第一次约会时,我后来嫁给的那个男人给我看了Footscray的微观经济。
那是一个周六的早晨,没有执照的小贩在街角卖草药、亚洲绿叶蔬菜、秧苗、山药油饼和香蕉叶蒸米包,他们从聚酯手推车里取货。
午餐时,他点了河内春卷,包上生菜和薄荷,然后蘸上鱼露。之后,我们在马里比伦农河(Maribyrnong River)河畔逛了逛波兰的一个节日,那里的摊位供应饺子和卷心菜卷。
他向我简要介绍了墨尔本内西区的情况:这里曾经以希腊和意大利移民以及向腐臭的河流排放有毒废物的屠宰场和工厂而闻名,后来成为一波又一波的越南移民的家园,他们在巴克利街(Barkly Street)开了面包店、越南河粉餐厅和发廊,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移民聚集在尼科尔森街(Nicholson Street)的非洲区。对于一个从珀斯荒凉的石灰岩郊区移植过来的人来说,这里是一个多元化的仙境,英国人的异类存在只是一道配菜。
在Footscray公园,人们可以一览洪泛平原和弗莱明顿赛马场(Flemington Racecourse)的全景。在那里,野餐者可以瞥见墨尔本杯(Melbourne Cup),以及一群醉醺醺、衣衫不整的赛马爱好者踉踉跄跄地走在受遗产保护的草坪上。
在尼科尔森街购物区附近,市政收入的支柱被亵渎——停车计时器受到公众的强烈抗议和频繁的破坏,最终导致议员遭到袭击。顾客们绕着常客们走来走去——一个越南男人,通常光着膀子,坐在长凳上的塑料凳子上,大声地唱着他的独角戏,这是一段散漫的即兴说唱,带着信念,挥舞着扇子。一位女士摇着装饰着农历新年装置的仿红包,希望能得到免费的现金,而舞台上的表演者则用歌剧致敬爱情、梦想、失落的土地和季节的变化。
在Footscray Markets,现金仍然是王道,此外还有储蓄者大商店(Savers Megastore)和便宜买英里(cheap Buy Miles),它们储存了超过“最佳食用日期”的剩余农产品(我曾在这里买到一大块布里干酪和一根素食火腿),它们构成了避免通胀的神圣三巨头。
在Footscray公园举行的婚礼野餐上,我们把一个空冰箱平放在草地上,装上了从Costco买的酒,把它变成了天空。我的丈夫堵住了一个现已被拆除的青石公共厕所里偶尔出现的同性恋声,预约了音乐家贾利·巴布(Jali Babu)用他的弦乐器科拉(一种西非竖琴琵琶)在派对上演唱小夜曲,并从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Asylum Seeker Resource Centre)招募了宴会承办商。他的大家庭半开玩笑地调侃道,在《疯狂足球》的狂野西部,需要穿防弹背心。空气变得越来越潮湿和压抑,直到雨云突然降临,笼罩着客人们,他们穿着毛茸茸的动物连体衣,在附近山上的水上滑梯上跳舞。
野餐变成了一个醉醺醺的夜晚。聚集在一起烧烤的苏丹家庭开始和我们的家庭融合在一起,直到我被一群孩子包围,让我评判他们的侧手翻比赛。“我没想到婚礼的门槛可以这么低,”一位朋友带着几分钦佩说。
这个社区的建筑风格五花八门,既有翻新过的小屋,也有铺着砖的贴面住宅,花园是用多肉植物和亚洲市场上的绿色植物在聚苯乙烯盒子里发芽拼凑而成的。我们住在一个破旧的、被列入遗产名录的维多利亚式双正面露台上。当我们第一次搬到那里时,我丈夫赶走了在车库后面的小巷里吸毒的人,以躲避街道巡逻队;但在我们家门口,一个人停在车里,吸毒过量而死。现在,这条街上住满了年轻的家庭,他们被更小的抵押贷款和更大的院子吸引着从阿尔伯特公园和普拉兰向西走。
学生合租的房子正在被崭新的装修所取代。惠比特犬和灰狗比比皆是。我们租的房子是这条街上最后的几处遗存之一,厨房的地板慢慢滑入泥土,等待着重新铺设——这种房子摇摇晃晃,但对孩子们来说很有吸引力,而且还会让一个朋友给我开一张福利支票,因为我这个千禧一代的老人永远无法达到成年的里程碑。在这里,我们可以用自家后院的鸡蛋和邻居交换烘焙食品、菲律宾炼乳果冻、河内绿豆饼、柑橘、辣椒和鳄梨,很难离开这里。
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爱丽丝·彭(Alice Pung)的回忆录《未打磨的宝石》(un抛光的Gem)激发了一个下午去她父亲的电子产品商店的灵感,在那里,她度过了十几岁的时光,与顾客争吵,推着穿着聚酯羊毛的兄弟姐妹们的婴儿车。作家汤姆·曹深情地讲述了他在Footscray社区艺术中心的一段工作经历——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每年一度的充气赛舟会漂浮在maribbyrnong河上,与往常聚集在一起的黑天鹅、鸭子和渔夫们在一起。钱景华(Jinghua Qian)在一个在线音频徒步旅行中描绘了Footscray的秘密历史,包括在天后庙遗址上的仁慈女神雕像,当你乘坐地铁前往弗林德斯街时,她的侧面轮廓轻轻地旋转。
在自传体小说《Anam》中,安德烈·道(Andre Dao)在叙述者穿越家庭记忆的同时,沉思着散居海外的越南人。萨拉·里奇(Sarah Ritchie)在特罗卡德罗拱廊(Trocadero Arcade)二楼秘密的五面墙画廊展出了她的烟熏和分层手绘醋酸版画,这里曾经是Footscray工人阶级经常光顾的装饰艺术电影院。
我想为社区同性恋酒吧的建立添砖加瓦,我们的足底之骄傲。他们被太多的请求淹没了,以至于兴趣表达很早就结束了。我带着当时七个月大的婴儿去看晚上的变装表演,他们的汗水闪闪发光,透过干冰。
这是一个睡衣可以被当做外套的地方,也就是说没有人会注意到。但有些人永远也进不去。我的朋友在Footscray车站下了车,检查了一间出租的房子,在站台上的街头斗殴中,他躲开了一把塑料椅子,乘坐下一趟火车回到了东郊。
周六早上的街头摊贩们时不时会被赶出去,以激活区里的中产阶级化编码语言。一个小贩卖给我们一罐高良姜,把它移植到我们的菜地后,长得像一簇竹子一样粗壮。我们不知道如何应对它的迅速扩散。我们只是看着它长啊长,把球茎编织在一起,就像一些复杂的编织。
Lily Chan是一名墨尔本作家。
这篇文章是The Age ' s Life in The Burbs系列的一部分。